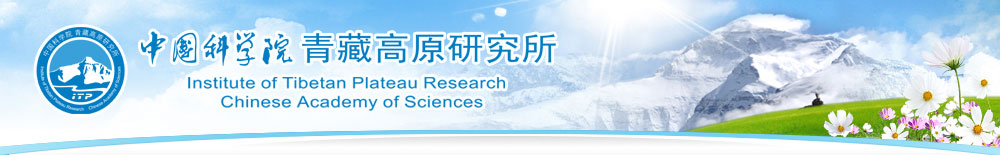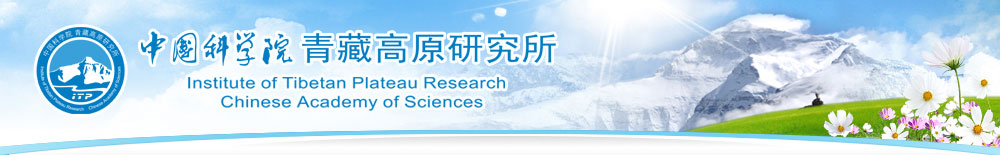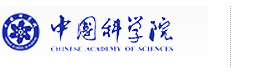2008年最新一期的《加州理工学院校报》专题报道了青藏所刘静研究员在四川省的实地考察工作。研究生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刘静曾积极参与了1999年美国墨迦瓦沙漠的Hector Mine震后地表填图工作。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周,即6月26日,她带着五名学生到达成都,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震后地表考察和填图工作。此间,刘静和她的学生穿梭于整个四川省,从南部开始,向北东方向逐渐转移,测量地震断层上的位移值。他们主要沿着主断裂带活动,有时候也折转到次级断裂带上。她带着学生顺着线索追踪,经过数日的不懈努力,发现地表破裂带超过200公里,长达近225公里。其中最大的断裂陡坎使地面升高了6米。在许多地方,地面抬高了2至5米。她还发现,地震破裂在北段是沿着一个主要断裂带逶迤,而在南部则触发一系列相互交错和连通的断层。
作为造山运动的典型区域,青藏高原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大陆,拥有八个世界最高峰,是地震活动的“火药箱”。高原座落在一个主要的板块活动带上,印度板块向下俯冲,托起了欧亚板块,周期性地引发大地震。她把印度板块的运动形象的称为铲土机,人们可以观测到这一运动、观测到运动是如何被不同的断裂带分解和体现、以及地震是如何释放的过程;并认为青藏高原上有不少类似于圣安德列斯这样的大型断裂带。
作为中国近30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紧沿着龙门山山脉。龙门山地区是中国地震活跃带,也是刘静科研工作的研究区域之一。通过对汶川震后地表的考察,她呼吁人们重新评估一些构造变形模型。她指出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强逆冲运动“表明了强烈的上地壳缩短量”。或许更令人警醒的是,汶川地震的活动指示了“位于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下面的隐伏活动构造的地震威胁”(隐伏构造指的是在地下发育的断裂带)。
在四川考察的那个月中,刘静他们几乎天天经历震级不小的余震。“地下遥远的深处真的有事发生,感觉起来不仅仅是摇晃,感觉上像是在磨搓。”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