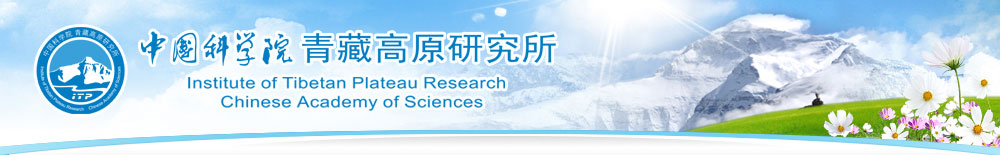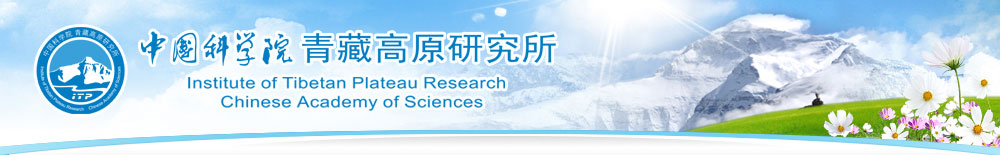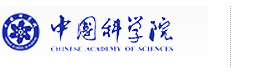|
(《科学在线》与新浪网同时发布:http://tech.sina.com.cn/d/2005-03-09/0849545163.shtml)
受 访 人:孙鸿烈,中科院院士
嘉宾主持:李存富,资深科学编辑
孙鸿烈简历
中科院院士。土地资源与土壤地理学家。河南濮阳人,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1960年为中科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生。1961年起任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助理研究员。1972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综合自然室助理研究员。197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4年-1992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委员(后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4月当选为中科院主席团成员。1993年10月当选为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副主席。1994年、1996年6月、1998年6月分别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1995年—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50年代起从事农业自然资源及区域综合开发方面的考察研究,参加了黄河中游、黑龙江流域、西藏高原和西南地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主持编写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开发和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报告和地图。70年代至90年代主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组织多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具体领导实施。提出了可更新资源的整体性、多宜性、区域性与有限负荷等特性,强调将自然资源作为整体系统进行综合研究。从全国性资源环境问题、区域性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战略、典型地区资源合理开展试验示范三个层次推动了我国土地资源开发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倡导并领导建立了生态系统试验观测研究网络,把资源环境的研究推向深入阶段。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2年被国家科委聘为“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的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1995年10月获“1995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技术科学奖)”。

[主持人]:
首先,欢迎孙院士在百忙之中到中科院网站的科学在线就珠峰科考和青藏高原研究做一个科普方面的访谈。问题是这样的:从今年3月20号到6月20号,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内有关单位,将开展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大型综合科学考察,这是本世纪我国首次对珠峰地区进行多学科的考察,也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考察。发起这次珠峰考察活动的背景是什么?珠峰科考在整个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孙鸿烈]:
今年这次之所以选择去珠峰科考,因为今年是从科学院第一次组织青藏科考到现在的珠峰科考正好3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时机。另外,今年之所以去,也是因为俄、有中国女子登山队要登珠峰,为了结合这次女子登山活动去考察珠峰。珠峰这个地区很特殊,海拔特高,假如没有登山队这个活动,我们科考人员去考察珠峰就相当困难,海拔太高了,有登山队,他们可能帮助我们考察和运送仪器样品等。之所以对珠峰这么重视,是因为它有很高的海拔,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具有很多特殊的科学问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珠峰特别关注,我们今年结合女子登山,又是纪念登山30周年,所以这次科考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在珠峰地区考察的时候,什么困难是对科考队员最大的威胁?
[孙鸿烈]:
氧气不足!你到了4000多米,像我们到拉萨才3600米,你在拉萨像我这么快速地说话就喘不上气来,在西藏的人,工作时间长了就好办了,我们刚到西藏时,一个月半个月,说句话就喘口气,到了五千多米,七八千米,登山的也要带氧气,不带氧气,8000米时就要出问题了,我们科考最多上五六千米,如果在那儿过夜,睡觉时脑袋就像要炸了似的,疼的不可忍受。
[主持人]:
现在我们的科考手段和装备,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孙鸿烈]:
作为科考来说,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装备,都备一些氧气瓶,是一些压缩的氧气瓶,很小的瓶子,我们在低海拔的地方,相对在西藏来说是低海拔的地区,在5000米以下,你必须适应,你老背着氧气瓶,哪有那么多的氧气供应,我们一般都是适应,5000米以上我们叫特高海拔地区,没有氧气就很困难了。
[主持人]:
珠峰科考在整个青藏高原研究中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孙鸿烈]: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些,它是特高海拔的地区,有特殊的一些环境,生物在这么高的海拔地区内,生物的特性,生物的适应情况,和一般的高原地面会明显不同。这里高度达到8000米,高出一倍的样子,因此它有很多特殊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我们很有兴趣;这也是冰川存在的地方,因此冰川的形成变化,研究起来也非常有意义,它是研究冰川进退演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当然因为青藏高原本身板块运动隆起,隆起最高的这个地方,它的地质构造和岩石的状况,也是对论证青藏高原的形成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些科学上的问题,从地质形成演化,从现代环境,到生物区系等等这些方面,主要是科学上的一些应用,在科学上意义是很突出的。
[主持人]:
从有关报道看,公众似乎更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珠峰的“身高”,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新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中有1700多处做了更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珠峰“身高”长了2米,原来是8848米,对这个珠峰身高的问题,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究竟用什么标准,什么方法来确定更科学,更合适?
[孙鸿烈]:
身高“高”了两米,从地图上看,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测出身高的。我们说的8848.13米,是我们30年前第一次登山的时候测绘组测定的,当时用非常精密的测绘技术,交叉测绘这个点的,这个点的上面有登山队员,登山队员爬到顶上,顺利地在上面树了站标,否则你没有办法交汇,当交汇以后才能测出来,我们30年前测出8848.13米,经过30年以后,这个高程有没有变化,所以这也是这次30年以后的科考内容之一,和登山一起去的除了科考以外还有测绘方面的目的,也是在30年以后看高程有没有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会有,因为珠峰不断在隆起,但是假如是冰层的融化,测绘的时候应排除冰的厚度,否则很难说是珠峰高度的变化,它应该以基岩作为它的标准,毕竟经过了30年,30年以后到底升了多少,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次再次测的目的,因为地壳在运动,总是有些变化,但是会不会增加两米,我倒要怀疑,毕竟我不是搞测绘的,不敢妄加评论,到底是多少,我们以这次测绘来对外公布。
[主持人]:
这次珠峰考察,我们选择了大气物理、大气化学观测研究,还有冰川变化监测研究,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变化研究,地质与地球物理观测研究,为什么选这几方面的内容作为我们的考察内容呢?
[孙鸿烈]:
刚才我谈珠峰科考的意义时,这几个问题都涉及到,因为生物的特殊性,地质构造特殊的问题,以及大气环流,那么高的高峰对大气环流带来的影响等等,那么高的地区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像低海拔的高原面上,4000多米,5000多米看不到的现象,在这个高度上都可以看到。这四个方面基本上也是概括了青藏高原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青藏高原研究无非是地球物理学,大气物理学,地表的过程和生物多样性,基本上也是这四个方面。而珠峰在这四个方面都是更有它特殊的地方。
[主持人]:
有关研究表明,珠峰的重金属含量像砷、硒浓度已经超过了长江和黄河,平均每升水中的砷含量,上世纪90年代比70年代增加了10倍,硒的含量增加了4倍,6000米处积雪样品的PH值达到5.8,环境变化如此之大,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孙鸿烈]:
这个数字我查了一下,是搞探险的一些人做的,他们提出了的数字,也是根据做了调查以后,包括别人做的,也包括他们做的,当时他们的判断是这样的:90年代中东那次石油大火,田燃烧后,带来了很多化学物质,化学元素随着高空气流的漂流,飘到珠峰沉吕矗馐且桓鲋饕脑颉A硗庵榉逭飧龅胤礁撸匀徊换崾堑钡厝烁先サ模潜鸬牡胤酱吹模獾闶呛廖抟晌实模卸谴未蠡穑还馐侵榉澹鸬牡胤揭卜⑾质钦庋模谴未蠡鹌暮芸恚中敲闯な奔涞拇蠡穑芏嗷г夭恕3苏飧鲈蛞酝猓嗖馗咴歉龈咴芏嗟推皆厍囊恍┢魉吹幕г兀强梢酝献叩模魃仙院螅匆恍┗г卦诟咴峡胀A粝吕矗庖彩且桓鲈颍词姑挥兄卸蠡穑鼋鲇捎诘推皆厍亩魉孀牌魃找院螅吹礁咴弦彩强梢圆摹?SPAN lang=EN-US>
[网友]:
从我们对外发布这次科考的预期目标看,把通过科普报道,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单独提了出来,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孙鸿烈]:
现在搞环境的都在强调公众意识的重要性,确实,要真正解决一个地区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完全靠着搞专业的人员,或者完全靠着这个领域具体工作的干部解决是做不到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关心环境,每个人都在关心生态的保护,你才能够保护好,这点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次既然是大的科学活动,也是引人注目的科学活动,当然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要做工作之外,结合起来做一些科普的事情,让人家知道,大高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忽然冒出这么高的山峰,这里的环境特殊,但有哪些特殊呢,正好可以做点科普,从整个青藏工作来说,也一直是比较重视科普的,希望广大群众知道青藏高原一些特殊的性质,以关心环境问题。
[网友]:
您认为开发青藏高原的旅游资源或者是登山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应注意哪些问题?
[孙鸿烈]:
旅游对青藏来说,是很重要的产业,特别是青藏铁路修通以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建议就是把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上日程,当地政府现在当然也很注意旅游的发展,对西藏来说,作为第三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作为旅游来说,我觉得不光是西藏,别的地方旅游也是这样,要增加公众旅游对环境的意识,不光是西藏,内地也是这样,到处扔垃圾,内地旅游点上垃圾乱飞,国外旅游点你去看看,那么多人我们也没有看到地上有垃圾,比如,你去了一些地方以后,要保护地方自然的植物动物,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旅游的同时,要加强环境的教育,刚才讲到为什么重视科普这一条,对今后中国旅游事业来说,不能搞旅游只想赚钱,在发展旅游事业的同时,也应该增加环境的意识,搞环境和生态的人结合起来,做一些科普的工作,写在宣传册子里头,我觉得对旅游者也是一种提高,他能够学到很多科学普及的知识,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国对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考察进行的较少,本次的科学考察,是否会对珠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进行考察,您认为对山南地区的考察有无必要性?
[孙鸿烈]:
对南坡的考察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次做不到。从南坡上去,我们要从尼泊尔的一些通道出去以后,从那边往上爬才可以。你从南坡必须到尼泊尔低海拔的地方去,从珠峰顶上过去是万丈深渊,因而过不去。南北坡的对比,你组织一次到尼泊尔的考察很费劲,包括物资的投入,也包括外交的途径,事情很复杂。我们南坡的资料是利用人家的资料没有专门组织考察队到南坡去。
[网友]:
您能否用科普一点的语言,概括介绍一下青藏高原和珠峰是怎样的东西呢?
[孙鸿烈]:
青藏高原隆起和板块密不可分。地壳有很多板块构成,印度板块发生漂移,和其它板块发生接触时候,就插在别的板块下面,进去以后上面的板块就给拱起来了,印度板块向北飘移,不断地插入把地壳给抬高了,造成地表的隆升。
[主持人]:
珠峰科考是很有意义的。从更广的层面讲,您曾作为整个青藏高原研究的领军人物和开拓者之一,当初把青藏高原研究列为国家的一项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其初衷是什么?近三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哪些有显示度的工作?
[孙鸿烈]:
从科学院来说,青藏高原研究,实际上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60、61年就开始组织西藏科学考察队,我当时也参加了,但是刚搞了两年,到62年就是困难时期了,我们就不得不停了,西藏自治区发文给科学院说,我这边吃不消了,所以也就停了,一停就停到73年。73年开始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断,30多年一直连续下来了。之所以对青藏高原这么重视,我想首先从国家需求来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青藏高原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4的国土,1/4国土的地区,你要发展它,当然必须对它的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而恰好这1/4的国土科学家对它的了解非常少,因为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海拔很高,4000多米以上,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在这样一个地区里头,噬衔颐嵌运母鞲龇矫妫拥刂省⒌乩怼⑸铩⒋笃龅厍淖匀换肪澈妥匀磺榭觯己懿磺宄晕颐窍氪庸业男枨罄此担枰哉飧龅厍邢晗傅牧私狻4涌蒲侠此担蛭嗖馗咴还馐侵泄模彩侨澜绻刈⒌牡厍飧龈咴蛭诩盖蚰昵埃歉龊#馐强隙ǖ模裁春罄幢涑陕降兀涑烧饷锤叩亩鳎颓3兜降乜窃硕奈侍猓蛘叽拥厍蛭锢硌Ю此担堑厍蚨ρХ矫娴奈侍猓飧龅厍茄芯康厍蚨ρУ淖詈玫胤剑右桓龊#涑陕降兀致∑鹞澜缱罡叩氖澜缥菁梗飧鲂纬梢院螅源笃妨鞔春芴厥獾挠跋斓鹊纫幌盗形侍狻6遥幕肪呈侨澜绾芴厥獾牡胤剑鸬牡胤胶苣押退员龋庑┪侍庠诳蒲咸剿髑嗖匕旅兀涌蒲а芯康慕嵌纫彩且俗⒛康氖虑椋跃筒丝蒲г合露ê艽蟮木鲂模度牒艽蟮娜肆ξ锪Γ?SPAN lang=EN-US>60年代,特别是73年以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在这个地区做工作。
[主持人]:
规模最大的是哪一次?
[孙鸿烈]:
规模最大的是73年开始的那一次,那个时候大概是73年开始,野外工作做到76年,这四年的野外工作,当时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这是规模最大的时候。四年野外调查完了以后就开始总结,总结了好多年,我们一共出了34部专著,这套丛书厚度有好几米长,就是这四年科考的成果,应该说是面上的考察,因为对青藏高原以前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比如说我是搞土壤的,青藏土壤是什么,你拿内地哪个土壤都对不上号,内地叫黑土的,拿到那儿对不上,环境不一样,土壤也不一样,完全要形成一套新的土壤分析体系,别的也是这样。很多动植物,全世界就没发现过,完全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首先得给它定名,属于哪个科的,哪个属的,新种要定名,这些东西都是在前四年里面要做大量的工作。等于一张白纸,一片空白,你要把它描述清楚,这个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地质构造,那时候是34部书,共40多本,可以说是记述有关青藏高原自然的一套百科全书。
[主持人]:
青藏高原研究的30多年,可以归纳出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供其他研究领域,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参考和借鉴。具体说有哪些呢?
[孙鸿烈]:
我很难说能让别人来借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来看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科学问题的目标必须十分明确,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就有很清楚的科学目标,比如前四年我讲的第一个阶段,总结是从73—83年,野外考察后,是陆陆续续十年的总结,出了很多本专著,我们的目标是对青藏高原各个方面的资源,自然资源的各个方面要做一个详细的普查,建立分类体系,它的分布和形成的规律,这个就是头一个阶段我们明确的科学目标。等到83年以后,我们进入了攀登计划,那就是说要选择若干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青藏高原板块运动怎么碰撞的等等这些问题,这就作为攀登计划一个明确的科学问题提出来解决。等这几个问题做到一定程度,解决以后,我们又进入五年期的“973”计划,又提出973项目的科学目标,973现在刚刚结束。十年左右的普查,五年的攀登,再加上五年的973,这样连续下来等于20多年的样子,中间还有总结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值得总结,每个阶段有个明确的科学目标。第二个我觉得值得总结的经验,就是必须要抓住一个问题,契而不舍,连续深入,否则的话,青藏高原的研究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62年终止以后,我们心始终不死,73年机会来了,应该说这些年一直干下来了。
[主持人]:
从73年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
[孙鸿烈]:
没有中断,野外研究和室内总结,有了目标要持之以恒,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目标。第三个感触就是,确实要形成很好的综合研究的团队,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多科学人才的参与,大家都是老搭档,一直在那儿工作下来,青藏高原研究从73年到现在,这么多年,可以说形成了三代人这么个梯队,以刘东生、叶笃正他们为首的这么一批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老师,这是第一代。第二代也许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70岁左右的这一代,形成了很大的队伍,73年以后的主力就是这支队伍。第三代大概都是50来岁带着二三十岁的这支队伍,也形成了很好的团队,这个团队真正大家是配合默契,大家坐到一起商量,一起摸爬滚打,随时交流沟通,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感动,非常可贵的事情,这些同志有的家里有很大的困难也不管,自己身体有点毛病,好了马上再进去干。从第一梯队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我们这方面的权威人士,都是老一辈的院士,都是权威人士。第二代,我过去算过数,但现在记不清了,大概出了十几个院士,参加青藏研究,或者以青藏研究为主要研究成果被评为院士的,如郑度、滕吉文等。73年以来因为大项目而成长起来了很多院士,就有十几个人。70年代到90年代以后陆续被选举为院士,如陈宜瑜院士,陈宜瑜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青藏鱼类的研究,滕吉文院士是因为对地球物理研究,还有几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大概有十几位先生。假如说,我们是不是能为别人提供借鉴还谈不上,但从我们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三条恐怕是作为青藏研究值得肯定的三条。
[主持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整个青藏铁路现在为什么进展比较顺利,这里面和科学院对青藏高原几十年来的考察,得到的科学数据是分不开的,现在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别的部门不可替代的,还有别的成果,在地方经济或者是在区域发展中正在发挥作用,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因为我想整个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属于一项很基础性的工作。
[孙鸿烈]:
我想青藏研究,主体就是基础研究的问题,我们也比较注意了,有一些带应用前景的问题,也列入青藏研究的计划里面,两方面都有的。纯粹从基础研究来说,这个道理很清楚,基础研究是什么,就是探索未知的自然规律,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总是要建立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特定的自然基础上,你对自然规律没有摸清楚,经济发展就很难做了。所以从这一点上,基础研究工作,也许当初做的时候,没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当时就是为了解决阐明自然的规律,但并不等于这个东西的结果对你的应用就不起作用。所以对于基础研究,是认识有关规律,不能强求任何科学研究,像过去有段时期,喜欢说没有应用目的的,就是没用的,这是非常短见的。当时研究青藏冻土的时候,程国栋院士在兰州冰川所对青藏高原冻土做了很详细的研究,当时他也不是为了青藏铁路,那时候还不知道要修铁路。青藏是冻土地区,他研究冻土的分布、形成的规律和变化。当时完全是从学科的角度,他知道自然界有这么个东西,要研究它,了解它,他做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自然的规律探索的。那时候绝对没有多少应用,现在修青藏铁路,成了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那个冻土研究,青藏铁路的修建还真是个麻烦。
[主持人]:
好像我们青藏高原考察完之后,出了好多东西,为地方经济,比如说西部地区发展,有的甚至从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这些建议的采纳情况怎么样?
[孙鸿烈]:
我想我们青藏研究积累了很多资料,现在对西藏来说,有关部门进行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据我所知,都是作为他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很难具体到选用了哪一条,但是基础的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必须要采用的一些东西。他们制定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我们这套书实际上等于是青藏高原的自然百科全书,你查什么材料,必须得用这个,西藏比如说哪个地方叫什么地带,哪个地方叫什么东西,就得查这个东西。西藏河流的水文状况、岩石的分类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以这个为主。我们在西藏后来也做了专门针对专门问题的咨询,这些咨询据我所知,都是送到国务院、西藏自治区的,比如西藏农牧业的发展问题,青藏铁路建成以后对西藏有什么影响,西藏要怎么样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基于青藏研究的院士咨询向国务院报,跟自治区领导谈,这些东西对他们启发很大。我在这里呼吁一个事情,问责制!我在呼吁这个事情,我们科学研究提了很多咨询,提给国务院,提给地方以后,必须要给个答复,你怎么采纳的,这个过去是不够的,我们只能从侧面了解一下他们怎么用的,但是你得给我回答一下。我给你咨询了,你给我回复一下,我现在作为院士建议,既然国家规定院士是有咨询作用的,咨询以后希望给我一个回复,你说我说的不对也成,你说你难以实现也成,但是必须要有个交代。
[主持人]:
您刚才说了,一个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另外一个是持之以恒,这里延伸一下,从我们青藏高原研究几十年来这么做下来,延伸到我们现在搞基础研究的,青藏高原研究的这些经验对我们现在国家整个对基础研究这方面,包括政策也好,一些做法方面,您觉得怎么样,应该怎么做,还存在哪些弊端?
比如说我们现在申请的基金项目,我看了有一个材料,去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美国基金会连续资助了他30年,我问您的意思是,假如这样的话,我们的基金可能做到资助三十年,四十年吗。
孙鸿烈:科技部的“973”计划这块我比较熟悉,我现在也是973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周光召是主任,973这块我觉得处理得比较好,它第一个强调的是你申请的973项目,必须要有明确的科学问题,另外一个是要有明确的国家需求,973项目是搞基础研究的,但是这个你要能想到你的研究能在国家应用前景上有用,不是马上应用,但是国家需求上要说清楚。
第二,在这个五年的973项目完了以后,经过验收评审,做得好的它会鼓励,继续给予资助,当然你需要再提出新的五年计划来,这点就比较好地注意到了它的延续性。
国家基金申请方面,这几年我跟他们打交道不多,一般面上的基金不太多,重大基金是不是也会对比较好的研究继续给予鼓励,连续支持,我想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考虑的。应该说P从973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青藏高原研究刚才我说了,如果没有科学院连续的支持,干上十年就停了,说什么你们青藏干那么多年了,该弄个题目给别人了,那青藏研究就没戏了。
[主持人]:
青藏高原属于中国,为我国科学家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它也是开展国际合作的独有平台,国际科学界对它的关注度、研究水平如何,我国科学家整体水平和特色如何,差距有多大?
[孙鸿烈]:
青藏研究,我们掌握的材料绝对是中国领先的,可以说我们对它是了如指掌。但是真正对于青藏研究来说,我们的创新性,现在不是提出要原创性的工作吗,这一点我们确实是不够的。比如说青藏高原,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当然可以用板块学说这个理论来解释它,但这个板块学说不是我们创造的,人家早就提出了板块学说,我们运用这个学说来阐明青藏高原,我们掌握了资料,可以说清楚,但原创性的板块学说还是在别人那儿,别的当然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理论是人家国际上已经有了的,我们用这个理论说明青藏这块东西,因为我掌握大量的材料,我可以用它来阐明这个规律,我们这点上,要说我们的差距,主要是我们在青藏研究上,如何在这么一个独特的地区里,我们真正能够做出原创性的工作。
[主持人]:
可能不应该说差距,应该说不足。
[孙鸿烈]:
不足也是差距,确实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恐怕应该在青藏研究这么一个独特的地方,地球动力学也好,地表过程这种规律也好,真正能够提出来中国的原创性的一些理论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地方。
[主持人]:
为什么谈到差距呢,是因为据文献资料统计,近20年来,国际上有关青藏高原研究的主要论文大概有3000多篇,中国的论文数是占第一,但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却是印度,好像我们中国是排在50名以后,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孙鸿烈]:
这是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有关人士统计出来的。一个原因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我们研究水平还不够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个问题,可能与我们的语言有关,我们多数的文章还是以中文发表的,真正以外文发表的数量仍比较少。这几年我们还是重视的,直接往《自然》和《科学》上投,因为我们在过去像七几年还没有SCI这个概念,我们尽管写了四十几本书,也没有翻译成英文,现在也没有完成这个事,现在注意到了,将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过去是不注意,这几年开始注意一些,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以中文发表为主,进一步像目前的工作,我知道,每年大概有一批论文发表在英文的国外的刊物上,这个对增加国外的引用率来说是会有用的,我觉得客观上应承认两条,一方面有水平不够的地方,另外,我想中国有语言上的关系,用用中文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人家引用比较困难,这点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进。

[主持人]: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是南极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这种说法在国际上的公认度如何,还是中国科学家自身群体对它的一种偏爱?
[孙鸿烈]:
国际上好像是有这种说法的,应该是公认的,因为南极北极,当然从地球的两端来说,各是一个极点,也说明这两个地方是最寒冷的地方,有很特殊的问题,青藏高原也是属于这么一个,它处在中纬度上,它反映出来严寒的条件,和南北极有相似的地方,把它作为第三极,正因为它高,有很多东西很极端,气侯、生物很极端的,第三极的说法在国外也在用,也在这么说。当然现在也有比如说臭氧洞,青藏高原上面发现臭氧层有变薄的趋势,包括氟利昂,亚洲这些地区氟利昂的排放,随着气流上升到高空上,上到青藏高原,和汇集到南极北极是一样的,这点作为第三极来说也是恰如其P的。
[主持人]:
您刚才介绍了30多年来,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收获了丰硕的精神成果,有人把它概括为“青藏效应”,请您介绍一下青藏效应的内涵意义和作用,还有个问题就是青藏效应,在目前环境下,是否仍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孙鸿烈]:
青藏效应的现实意义,应该是很大的。关于青藏效应,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科之间要有很好的协作综合,特别在地球科学或者宏观生物学这方面,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是解决一些问题必不可少的。
地学和理论物理和纯数学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光靠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学科就能够阐明这些问题,青藏研究中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都是很多学科在那里共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一个结论来。第一点,青藏效应里面,能够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各学科、各科学家之间能够互相取长补短,能够和人家合作,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青藏研究能够之所以一直坚持做下来,我们觉得是值得总结经验之一,也是感觉这条的重要性。
另外一条,青藏效应,我想我们不光是一个科学研究,能够把科学研究工作和人的培养结合到一块,本身科学研究当然也是人才培养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应该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给他们提供一些条件,另外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条件,让这样的梯队一代一代地接下去,团队精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再一个内容,我觉得从青藏效应来说,我觉得一个科学家,他不光是一个只是做科研的,我觉得他恐怕还有一个精神面貌的问题,因为青藏确实是比较艰苦的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有一种勇于面对困难,甚至是献身的精神。确实,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在青藏高原牺牲的,就是这么一种献身精神,有的人常年或是半年离开家,在高寒地区那么奋斗,假如没有这么一个干劲,没有这么一个精神面貌,我觉得很难做好青藏工作。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能够说青藏效应第三点的话,那就是精神面貌很重要,光说科学,钻研搞科学,当然这种精神需要,但是除了这个精神之外,我觉得还要有一个勇于克服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我觉得这样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主持人]:
孙院士,青藏高原的隆起应该说是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各国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它隆起带来的环境变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想问,我们国家在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有哪些考虑。
[孙鸿烈]:
这些年来我们比较注意青藏研究的国际合作,我们举行了几次以我们为主的青藏高原国际研讨会,我们的目的试图把中国方面的工作介绍出去,另一方面,希望请一些外国科学家来,了解人家做的怎么样,有的人没有到过青藏高原,但是在外部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也想吸取他们的成果。除了这些国际会议的形式之外,也组织了重大的联合科考,这些联合工作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看来今后越来越多的外部科学家会进入青藏高原,怎么样更好地吸取人家的一些长处,把大家对青藏高原的认识及时地进行交流,得到互相的学习机会,这一条始终是我们值得注意的。现在当然也有了条件,因为现在年轻的同志接上来以后,这一代同志的英文能力都相当强,这样的话对国际交流带来了很有利的条件。
[网友]:
联合国环境计划年度报告(2004/5)介绍了中国科学家关于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冰川消融的研究。报告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冰川退缩强于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转入全面退缩状态。您作为评价这一研究结论?它对于我国乃至全球,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如何?可以确定冰川消融是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么?如果遏制这一趋势呢?
[孙鸿烈]:
这是个事实,我们自己研究也得出了这个结果,这与全球变化中气侯变暖有关系,全球变暖这个趋势仍在继续,青藏高原的冰川明确是在退缩,比如说,冰川长度原来是10公里,现在变成7公里、8公里、9公里,就往后缩了,冰川长度减少,冰川湖泊的水位上升,这是现实情况。这是个趋势,假如全球变化趋势继续下去,冰川融化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主持人]:
这对我们国家甚至全球,近期远期的影响怎么样?
[孙鸿烈]:
冰川退了以后,因为青藏的河流,主要是冰水融化,增加了对河流水的补给,这不是降水直接补给的,这样在高山上形成积雪冰川,再慢慢地融化下来补给河流。西藏的水文状况,冰雪融化补给作为它的主要来源。因为气候变暖以后,河流水量会增加,湖泊的湖面会上升,这是必然的现象。这个现象对西藏来说,从近期来说,它未必是个坏事,河流的流量补给大了,但是这个趋势,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一直是这样,因为施雅凤先生现在研究的结果,认为中国的北部,现在的问题随着气候变暖,湿度也会加快,变暖可以有两种组合,一种是暖干,一种是暖而且湿,确实现在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施老的说法是对的,有的地方随着变暖的过程降水量P增加了,如果这样对青藏高原来说,一方面变暖以后,冰川会融化,但是高山上的降水量也会增加,冰雪的补给也会增加,这样平衡下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亏了还是盈了,确实是个问题,青藏高原的问题始终研究不完,新的情况出现了,又值得研究,今后随着气候变暖,变湿的过程,青藏高原降水量会增加多少,融化的量占多少,这个平衡下来以后,因为假如没有这个降水量增加的,冰川融化完了就完了,水的补给都没有了,就出现问题了。当然你说青藏高原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青藏是亚洲很多大河的上游发源地,包括长江、黄河、湄公河,都是青藏高原的发源地,它们的水量增加,对下游水文状况有很明显的影响,这点是对的,但是你要说青藏高原,随着冰川变暖以后,对全球气候带来什么影响,要进一步地进行研究,这方面研究现在不是太多。
[主持人]:
您既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优秀的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如何总结国家对青藏高原基础研究这方面的得与失,或者说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今后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
[孙鸿烈]:
你说我是科学家是可以的,应该把“优秀”两个字去掉。从我们工作看来,对基础研究来说,以前总的投入是太少了,基础研究这块始终形不成太大的力量,这些年,逐渐在加强,这当然是很好的趋势,而且刚才我说了,基础研究现在也比较重视连续性的问题,看准了,基础研究就要坚持下去,但前提是你必须做得好,前五年做砸了以后谁支持你,对做得好的继续给他支持,这条都是对基础研究规律认识的结果,加强了投入,给予连续的支持,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方面。现在对基础研究,年轻的力量不断地涌现出来,国家在基础研究现在逐渐形成了一支基本上以年轻队伍为主的这样一支团队,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前提,对中国的基础研究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网友]:
2004年的全球和平奖授予了非洲的女黑人环境科学家,我国研究青藏高原的科学家当中,您认为有没有可能因此在这方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而打破我们本土科学家一直与诺奖无缘的局面?
[孙鸿烈]:
可能性当然存在,中国科学家应该有这个志气争取得到这个大奖。现在我们在近期里,恐怕还有困难,困难刚才我说了,我们很大的差距是我们在这方面原创性的工作很少,我们很好地解释了青藏高原怎么形成的,但用的是人家最基础的板块学说来解释的,创造板块学说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你用这个来解释了,解释是很大的贡献,但是诺贝尔奖还是讲究对原创性的认可,这点我们还是有差距的。青藏高原这块地方,确实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太多了,如果我们在青藏高原研究的某一方面做出了原创性的突破,我觉得,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从您个人经历来说,您如何理解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当中的作用和意义?
[孙鸿烈]:
从人类进步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当然是主要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面,在自然中求发展,对自然规律你要有清楚的认识,循着这种规律去发展,这个路才能走对,违背这个自然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就谈不上,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教训我觉得是非常之多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以认识自然规律为它的基本任务的基础研究是十分有用的,我觉得对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真正能够认识,善待地球,适应地球,我觉得科学绝对是重要的。
[主持人]:
现在我们都讲和谐社会,恐怕人和自然的和谐更重要。
[孙鸿烈]: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基础。你说像58年的大跃进,能和谐得了吗,天灾人祸,违背自然规律地硬干,大炼钢铁,弄得水土流失,灾难性的后果就来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假如我们基础研究很强,虽然科学家也懂得这点,但是基础研究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没有给它施加社会影响的这么一个机会。假如基础研究能够给了很清晰地说明,把规律说清楚了,而不是一般泛泛地说,而是深入地把规律揭示清楚,决策者认识到这样,他们就不会蛮干了,这一点也许中国更值得从我们过去深刻的教训里头能够懂得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问题。
[主持人]:
作为一个知名科学家,您对年轻人科研工作有何建议呢?
[孙鸿烈]:
现在年轻科学家确实是非常有潜力的,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更为现代一些,接收了比较系统的学习,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会儿搞运动了,一会儿怎么样了,他们的理论相当扎实,和国际交往的能力,外语的水平都很强,特别从青藏研究来说,我们有过去很好的一些基础,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的条件,我觉得恐怕从年轻一代来说,更要注意的是能够比较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工作,不要急于求成,这点恐怕现在我觉得是很值得重视的事情。
[主持人]:
特别是现在说的所谓浮躁问题。
[孙鸿烈]:
这点我觉得不应该怪年轻人,跟我们的政策也有关系,我们的政策一切都和SCI联系起来,和政策引导有关系,其结果就是这样,对于年轻人会想到,SCI怎么才能多呢?第一,我选一个比较容易突破的事情去做。第二,研究群体人数少一点,甚至一个人做更好,最多两三个人,否则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呢,如此这样下去非常不利于像地球科学的发展,有的学科可以这样做,但对于地球学科会很影响大家的团队精神,很影响大家真正扎扎实实地做事情的积极性,结果大家都很急,急于出SCI论文。对理论物理,或者搞纯数学可以用SCI评价,不同的学科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假如没有这一条,会影响一代人的成长,我觉得是这样的。
[主持人]:
谢谢孙院士,谢谢各位网友,本次访谈结束!
|